自杀未遂的人会生活得更好吗?
2024.8.1
下午5:06,我当着母亲的面服下了除草剂。
喝下除草剂前,我甚至提前付清了所有的尾款。
父亲回家后才开车拉我去了医院。
他们太紧张了,我甚至进了抢救室,还被下了病重通知书。
而我仅仅只是感到了胃部的灼烧感。
但还是有些道理。那些剂量的除草剂确实可能致命,虽然我并不是很在乎。
我刚好挑到个全市都测不出成分的除草剂,这导致无法得知我是否会有生命危险。简单来说,我如果现在回家,可能会在几天到两周内突感不适,但为时已晚。所以,血液透析是最稳妥的。
关键是,母亲还很损地把农药瓶里剩的全倒光了。于是什么成分不知道,喝了多少也不知道。
感觉自己好像“薛定谔的猫”,不知是生是死。
其实我的内心是毫无波澜的,我早已做好了赴死的准备。即使活下来也只是给我添了麻烦。所以,我宁可死。
危险期内,我暂时住进了监察室,身上各种各样的线使我连上厕所都麻烦不说,还得被迫遭受监护仪的吵闹。
监察室内尽是些行将就木的老人,痛苦地苟延残喘着,却只能得到护工的骂声。
恐怕他们活着只是为了能提供多些退休金给子女吧。
我抚摸着那些连接着身体和监护仪的我不能完全明白原理的东西,想着“原来这样的仪器就能一视同仁地检测出任何人的生命体征”才惊觉原来这与其他人别无二致的囚笼一直都在如影随形着。
真是够讨厌的。
其实房间内神志不清的大家要是能有够一刻回归清醒,一定也是这么想的吧。
那些老人如此任人摆布地活着,一定比我要痛苦得多吧?
真不敢想,就连幸福的我都在无时无刻地不想一死了之呢,更别说那些可怜的老人了。
当然,我能理解他们的子女,这么做也一定有他们的苦衷。也许他们急缺这笔退休金、也许他们正在施以报复、他们也可能压根就不存在……
我不打算透析。时候到了,就看我的造化吧。
晚安,愿我一觉不醒。


2024.8.2
昨日一整晚都在持续不断地输液葡萄糖之类的液体,再加上之前抽动脉血的地方传来的酸痛,我彻夜未眠。
待到下午小晴来看望我,我也正好要从消化科转到精神料。
这里的精神科最令我感到不适的是:病区禁止出入!就连有家属陪同也不准!这就意味着我的活动范围被限制在这小小精神科的走廊与我的病房里。跟坐牢没多大区别。
经历了这种变故的内心是极其脆弱的,在这种环境下,我很难不去担心自己是否会抑郁。
病房里仅有两个床位,隔壁床是18岁的双相情感障碍患者小李。
小李看上去病得严重,会时不时盯着手机说胡话。她母亲看着我和小晴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想必心里也不是滋味吧?
果然,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永远不会简单。我仅仅只是上了个厕所,小睛便坐在我的病床上哭泣了。
出于情谊,我没有理由不上前安慰。
因为考虑到空间不足,我只得用吊着水的那只手将小晴搂入怀中,并轻声安慰着她。
善于安慰别人是我值得骄傲的长处,极强的随机应变能力使我永远都能安慰到最重要的点子上。
不过,处于特别关心病房,身着病号服,手上扎着留置针,胃里还残留着灼烧感的我,不仅表现得是如此无恙,还安慰起了来看望我的朋友,总感觉有些违和。
晚上,我无意中听到小李的母亲问她:“你不好好控制,打人怎么办?”她答:“不知道。”
我听后心里一惊。虽说不是没有的做心理准备,但就算是一个亚健康的人跟带有攻击性的精神病共处一室,总归是会害怕的嘛。
可以说,亚健康的我是最容易任人宰割的了。
2024.8.3
我胃里灼烧感被替换为了轻微的腹痛。
挂东西的杆子上怎么还有别人上吊过的痕迹啊?
也算是意料之内了……

隔壁床的小李总是哭诉自己控制不住想打人的想法。
我不明白,我为什么要和这样的人一样住院吊水。
难道我跟她一样有问题吗!
我从未伤害过任何人,我只是稍微想为自己考虑考虑罢了。我有什么错?错在我不该为自己着想?
那些医生像是很在乎我那微乎其微的自残似的。为避免误会,我只好郑重声明自残是不会给我带来任何的快感的。偏偏查房的医生哪壶不开提哪壶。她竟然问我做什么事情会有快感。
如果是其他人问我,我当然会十分骄傲地回答:“那种事情是不存在的哦!”但在这种时候,我的骄傲竟褪了几分。
通过手上那个一直在碍事的留置针,我被静脉输液了地西泮。这是一种偏向于用作镇定的药剂。
难道我表现出的活泼开朗被讨厌了吗?好生气!这明明是我竭尽全力所表现出的我自认为最好的状态!
世上也就只有她能看见我为这人设所付出的努力。只有她会认可我的这份努力。只可惜,我这辈子大概都不会再见到她了。
小李的母亲问我:“为什么要得这个病?”虽然心中有些怒气,但也只是笑着回了句:“我没病啊?”然后得来一句:“心态挺好的呀。”我挺高兴她能这么觉得的。
住院真的很令我烦燥。遇见来看望我的小林同学小跑几步都要被看见了的护士问话。午休时间说话稍微大声了些,就被隔壁小李的母亲嫌吵到自己睡觉(至于小李,她已经被打了镇定剂昏睡过去了,呼噜声可大了)。当然,我之后便没再出过声了。
下午4点半,精神科狭小的走廊上响起了嘹亮的喊骂声,是一个女人在用我听不懂的粤语朝着家人骂着什么。就连小李都被这动静吸引,走到走廊上围观这场骂架。
但这着实不太礼貌,于是护士便,将大家都赶回病房了,就连站在门口观望的我也不例外。
后来通过她哥了解到,她患有双相情感障碍原本是同意住院的,结果到了地方却又忽然翻脸了。
小李今天被给了四次安眠的药剂,这导致她几乎一整天都是在睡梦中度过的,没醒多久就又睡着了。甚至有一剂临时添加的药是在她母亲的不知情下给小李服下的。
开药的医生说,是因为她感觉有些狂躁,而且总嚷嚷着想要打人。担心她伤到其他病人,所以有必要的时候会临时加药。
我认同小李母亲的说辞:小李只是有点情绪,跟医生聊聊天就好了,没有必要加药。
毕竟,我从她母亲口中得知,小李从未打过人。我虽无法辨识真伪,但至少她从未伤过我。
这样永远也睡不醒的状态对于一个活生生的人来说实在是太过于残忍了。既没有活着应有的行动力,也没有死去应有的宁静,因为即使她处于那宝贵且短暂的懵懂状态时也是烦躁不安的。
天呐……这状态可比死亡要惨上数万倍啊。
为什么要我住院啊?难道就只是为了告诉我:“你只是个苦都没吃过多少的烂人,配不上甜蜜且美好的死亡”吗?
可是,我一点也不喜欢活着的感觉。这对我来说太痛苦了,不是吗?
不过,也就只有那位曾经在我身边的她能看见我的痛苦了。真希望这辈子能再见她一面,和她再说一句话啊。不过,没准死后就能见到她了?说不定呢?
2024.8.4
与昨天一样,依旧是上午6点半准时起床并伴随着轻微的腹痛。
这里所谓的日常治疗是离开微电流刺激仪的啊,就是用两个耳夹夹在耳垂上,让人感到不太舒服。我第一次见这玩意时就在想:“没有耳垂的人该怎么夹?”
原来这家医院每天就只会注射地西泮啊。明明那就只是会让人感到困倦的药剂而已。
随着冰凉的液体注入我的静脉,身体似乎也开始不受控制了。我讨厌自我失控的感觉,因为这会使我感到对自我的掌控感缺失,让我失去安全感。
今天,隔壁床的小李已经锤击了好几次床垫了。
即使医生给她一天到晚几乎不间断地下镇定的药,但她一旦不处于昏睡状态下就会一直吵着要打人。
就这么点大的地方,旁边的人还吵闹个不停。她就连睡觉时打的呼噜声都响彻云霄!
房间里的噪音从不停歇。不是响亮的呼噜声,就是吵闹声。
虽然我没有想要责怪她的意思,毕竟她都病重到会时常尿床了。但事实是:嘈杂的声音永远都会使我感到烦躁。再加上我需要极力压制缺失安全感所触发的我那特殊保护机制,我是真的快要撑不住了。
小李的母亲也不是省油的灯。她怕冷,于是总是悄悄把房间的窗户打开放外面的热气进来。并且只要我不去关,她就永远不会主动关窗户。
但我又是一个极度怕热的人。我平时在家,就连空调开高了一度都会热得浑身是汗,更别提现在了。
好烦,好烦!好烦啊!下午1:40,小晴给我打电话找我倾诉。可偏偏当时的我既崩溃又因药物而感到头晕。还被父母以担心吵醒小李为由喊去走廊上打电话,极度崩溃之下的我自然是不想妥协的,何况小李平时也总是吵闹、走廊上有着那么的多人……待父母离开房间后,我才稍微有了些松懈,随后极力调整着哭腔继续安慰小晴。
我知道自己表现得很怪异,所幸并没有人看见这狼狈的一幕。
小李因自己的进食障碍跟她母亲吵起来了。她坚持自己要减肥,但她母亲却表示这样下去小李的身体会一直出问题,她又没法照顾自己,所以照顾起来会很麻烦。
小李说自己两个月前暴饮暴食,但其实也只是重了4斤而已。于是她就开始有意识地节食,到现在甚至什么也吃不下了。
我作为利已主义者完全无法理解这种行为,我是压根不会在意别人对我身材的评价的。
下手4点半,护士叫我出去填表。
那个心理测量的表我是以最快的速度乱填的。除了关于“对异性感不感兴趣”那项外,我全部都填了最好的那项。
开什么玩笑?要是真的按照真实情况填写,怎么样都不会有好的结果吧!我可是长过教训的。上次我在别的医院住院就是因为没有防备地袒露了自己的真实情况,结果开的药使我痛不欲生。
我才不要在这种地方跌倒两次呢!我会记住:我真正的盟友只有我自己。
原来小李总是拨针的原因是喜欢血腥的东西,所以看到拨针冒出来的血会有快感哪啊。她说自己喜欢一地血,分尸装袋之类的画面。
我告诉小李:“我是ドS哦!”结果她告诉我,她只是想报复社会……虽然感到了不适,但我还是选择发表一些擦边的涉政言论,可惜她好像对涉政言论不感兴趣。
晚上,我最担心的事终于还是发生了,我如在此处的每一天那样躲在厕所无声抽泣时,小李在门外要求上厕所。我自知理亏,只好一边强行刹住眼泪一边用纸擦去明显的泪痕。然后平静地开门。
在这里,就连哭泣的时间都会被限制。
小李说:“医院不就是来释放自己(打人)的。”“那你打的也是别人的宝啊。”“别人的宝关我屁事?”“对啊,关你屁事。谁会给你打?”“我乐意。”“那人家不乐意啊。”“人家不乐意关我什么事?”她母亲又表示对方会还手,打不赢的。她说:“我打不赢也打。”对话到此结束。
虽然知道她是精神病患者,但我依旧鄙视她。因为在我个人的认知里,无故伤人就是不对。
我就连哭泣都会为了不影响别人而跑去厕所,而她却想要打人。
我受够了。明天,无论如何我都要提出要出院。
2024.8.5
虽然依旧是6点半醒的,但我一个回笼觉睡到了九点多。腹部还是有些痛的,但也算是自作自受了。
醒来时医生刚好在查房。为了有利于出院,我如实交代了住院的原由。当然,我会隐瞒喝除草剂的某种动机。
父母告诉我,因为我是喝除草剂进来的,所以办医保需要审核。真是的,拉我到医院前也不想想。不来不就没这么多事了吗?
我又不是喝了一桶除草剂,要是那么一点除草剂就能杀死我,那也能算作是自然淘汰了。
医生找我谈话了。明明我已经解释过自己这么做并不是冲动自杀,她却说什么:不了解我的,是个人都会觉得喝除草剂这种事情很匪夷所思。还说住院可以帮我探索自己做这种事的内心动机。
那种事情我当然是在心知肚明后藏在了内心的深处啦!怎么可能会随便往外说?
问为什么不说?当然是因为我要保证这样重要的东西不会受影响而改变啊。
结果对方说出了让我哭笑不得的话:“我们没有要改变你啊。”我听后表面上不动声色,心里却在发笑:“我又不傻,大家的目的不就是要改变我的驱死观念吗?”
不过,我倒也不在乎他人的想法,于是便没有出声。
好吵啊,小李一天有20多个小时都在打呼噜。我肚子好痛,也许是因为噪音所导致的应激反应吧。我好崩溃,但我能做的只有偷偷蜷缩起来抹眼泪。
我都快要开始后悔没有一口作气地完成真正的自杀了。
下午3:20,心电图和脑电波的检查单终于开下来了。做完所有检查后就差不多可以出院啦!
不过我已经猜到检查出来的指标概率是有问题的了。毕竟我现在一直都处于崩溃中,而非那个我一直以来的平常状态。
下午5点,我做完今天两项检查就换病房啦!
远离了那个想打人却只敢打自己母亲的小李后,我的舍友换成了看上去没有攻击性的22岁焦虑症患者小陈。她很安静,几乎不说话。我对此比较满意,至少我不用再每时每刻都被密不透风的噪音包围了。
小陈是做公诚咨询的,她会因工作上的一点小差错而耿耿于怀。也许,她就是为了不让自己的状态影响工作才来住院的吧?这种事听起来似乎是屡见不鲜的。最初,我也是为了自己的学业才开始吃精神类药物的。
晚上8点多的时候,刚结束崩溃状态的我突感困倦。虽然很不情愿,但也只能妥协了。
直到晚上11:06,我总算夺回了身体控制权醒了过来。
我还没睁眼就注意到了脚上传来的不适,坐起身一看才发现是两片膏药。我知道那是趁我睡着时贴上的,而我却完全没印象。看来那时睡着的我也算是某种意义上的不省人事了。
醒来后,我只感到十分后怕。我接受不了这种莫名其妙的昏睡发生在我的身上,这对我来说比突然死掉还要可怕。我是真的非常害怕自我失控与对自我的掌控感缺失的感觉的。
真不知道是什么药物把我折磨成了这副样子。
2024.8.6
凌晨0:18睡,上午6:45醒了第一次,上午8:38起了床。胃依旧在微微发痛。
母亲说,在我睡着的期间,小陈连敲鸡蛋都因害怕吵醒我而不敢大力地敲。这导致敲了好几次,鸡蛋都完好无损。
其实,她没必要这么做。我是很讨厌自己不受控或是不合时宜地睡觉的。我手上的一道道划痕正是我对上学期间的自己在富马酸喹硫平片的支配下在老师讲课时睡觉的惩罚。
9点多,要做抑郁、焦虑自评量表了(SDS与SAS)。
看到那些无关紧要的小事被标上了病态的分值,我的心中五味杂陈。
医生说要如实填写,我“宕机”了。
但转念一想,我的真实情况又到病态的程度,没什么必要藏着掖着的。意识到自己不需要抱有这么强的戒备心后,我便根据真实情况稍微控了分值,填写并交了上去。
为什么还是要住院啊?在医院精神会一直处于紧绷状态,长久以来的话我可受不了!
一刻不停地表现出精神焕发的样子使我简直快要筋疲力尽了,但又因某种原因不得不将这样的亢奋状态维持下去。要在陌生的环境露出自己柔软又脆弱的“内胆”的话,我就会很没安全感的!
下午2点多,跟母亲吵完架后就做了核磁共振和CT。所有的检查环节大概是结束了。接下来可以商量出院咯!
我妈带来了隔壁病房11岁的抑郁症患者小盈盈。但还没聊几句,她就被叫去做我拒绝做的团体治疗了。
我担心刺激她,便没有过问她的经历。但我还是会不由地想:究竟是怎样残酷的社会让11岁的女孩患上抑郁症啊?
下午3:31,那个曾在走廊上骂架的32岁女人忽然在走廊上叫往了我,非要拉我去聊天。
因为见识过了她的实力,所以我接受了邀请,带着好奇上了她的病床。
她的思维相当混乱,和我聊天的过程中时不时与其他人说几句粤语,导致我根本听不出连续性。不过就算我听得懂粤语,我大概也听不出什么逻辑性。上一秒还在问我“2999的电视你要不要?”下一秒就凑到我耳边神秘地说“我哥像你男朋友”什么的。其实我真的很想告诉她自己是女同性恋这回事。
聊着聊着,我便掌握了和精神病患交流的诀窍了:只要一味地肯定就够了,因为他们很忌讳他人输出不同观点。
后来我得知她的名字叫作“婷婷”,这是我在现实第一次见到叠字的名字。
下午4:34,做完团体治疗的小盈盈得知了婷婷的事后,便要求与我一起去见婷婷一面,于是我们一起听她讲了十多分钟的胡话。
婷婷虽然思维不大清晰,观察力却出乎意料的还不错。她竟然注意到了我手上的划痕,可我平常分明会下意识地用袖子遮掩那里啊。
下午5:15,我在去护士站做问卷的路上,偶遇了婷婷,于是我朝她礼貌地露出了我的招牌微笑。结果被路过的老奶奶却告诫我不要对着这样的病人笑。
我不顾自己的痛苦不就是为了将灿烂的微笑赐予大家嘛!结果却遭嫌弃了呢……好失望。
下午6点,我看着最后一份问卷陷入了沉思:自杀态度问卷(QSA)。
如果要认真填这份问卷,我就要在表现出反对自杀的观念的同时符合我喝农药的行为。
难度太高了!于是,我干脆除去一些过分的选项后,全部都违心地填上了“中立”选项。
在如此没有安全感的状态下,怎么可能会有人将自己的真实情况全盘托出?
下午7:41,婷婷来到我的病房门口找我,以“给男朋友报平安”为由借走了我的手机。结果他一拿到我的手机就拨了“110”这个报警号码。
我一瞬间便反应过来了,但我不敢去抢回自己手机。最后还是由我妈以我的名义抢回来的。
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她在混乱中被抢手机时竟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反抗。
她视所有人为敌,却唯独不会伤害我。
我想起她曾经对我说过“只有你理解我”这样的话。想必,这意味着我已经获得了她的信任。
婷婷的信任其实很容易就能获得,只需要有足够的耐心陪她聊聊天就够了。
晚上8:48,我再次莫名其妙感到了困倦。于是只好不受控制地睡去了。临睡前还因乏力而被迫让父母替我给我的手机充电。
与昨天一样,这样的昏睡只持续了3个小时左右。我在晚上11:49时醒了过来。脚底依旧在我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贴上了膏药。
这是我一天之中最没有安全感的3个小时。
2024.8.7
凌晨0:35睡下,6:23起床。我似乎已经有些习惯那轻微的腹痛了。
今天,我终于要去和医生谈谈关于出院的事情了。昨天,晚上医生找过我的父母,因为她不知为何觉得出院是我父母的意愿,而非我的。
早上8:25,周医生来找我谈话了。
谈话过程中,我发现她一直在强硬地偷换概念,不断地将话绕到治疗与药物上。明摆着一副“我说什么就是什么”的样子。
不过我倒是没兴趣跟医生争辩,仅仅只是绕着“死掉就能解决的事,不需要花那么多功夫”的观点为中心,稍微有些气不过地表达了自己的不屑。
最后协商的出院时间在周日。
周医生想要我输液利培酮。我在得知了该药的副作用后暴怒。我很担心这会影响我上学的能力。
我要是连正常地上学都做不到,是绝对会被自己字面意义上的“气死”的!我一旦察觉到自己彻底失控,那么这段该死的人生也算是到头了。
我得去找周医生聊聊。
上午9:41,母亲带我去医生办公室找到了周医生。
不出所料,医生永远都有自己的那一套。无论如何都要让我试试口服利培酮。
最后,她说的话彻底激怒了我。她以我“带着吊瓶来找她”为锚点说我焦虑!
我本身就对母拎着吊瓶来说这点事感到不满,再加上跟医生不愉快的对话与我住院期间脾气就差。于是我干脆直接在原地就崩溃着大发雷霆了。
下午11:14分,小盈盈来找我了,说是想让我帮注册Apple ID。
眼看时机成熟,我开始问她抑郁的原因。原来,仅仅只是父母的争吵与朋友之间的矛盾就能让人抑郁啊。
回想起我的小学时光,是同班同学的肢体霸凌,是因学习原因或是成绩稍微下降而遭到的父母打骂……父母的争吵与朋友之间的矛盾自然也不可避免。
可我却不折不挠地熬过了小学的学业。
可惜,现在的日子于我而言,更是地狱。
所以我就算自杀也是理所应当的!没有任何人有资格对我的这项选择指手画脚!
我母亲还非要说什么:“每个人的感受不一样。”那难道我就活该痛苦吗?
时隔多月,我再次下意识地绷紧了肌肉——那是我处于焦虑中一贯的表现。
如果没有母亲提及,我大概会将这份焦虑直接忽视掉。
看来住院不仅使我崩溃,还将那份我许久未见的焦虑带了回来。
我在热敷中药的时候突然发现,我的腹部一旦受到热敷就会疼痛。这样下去的话,我以后痛经就不能热敷了呀……
4点半,母亲根据我的情况决定去和周医生商量明天出院的事情。
可惜我太累了。已经没有力气去医生交涉了。
迫不得已,只能由我母亲代劳了。
最终也算是谈妥了。通过母亲转述,周医生表示:“要走就走,回家有什么后果你们自己承担。”
我感到庆幸:幸亏我没有去。
真是的,难道在医院后果就由她承担吗?由她来帮我承受住院的痛苦吗?
拜这段住院时光所赐,我回家后还要花不短的一段时间将住院导致的崩溃状态“清洗”到可以正常上学的状态。
待到明天出院,我还要面对新的难题:在开学前的紧迫时间内调整回住院前的状态。真是郁闷啊。
其实在我的胸膛里一直塞着一股不安:我真的能在仅仅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从近乎完全崩溃的状态转变为活泼开朗又善解人意的状态吗?
至于为什么我现在才考虑到这个问题?因为我之前一直都深陷在住院导致的痛苦中无法脱身啊!
明明已经尽可能精打细算了,为什么我却还是低估了住院对自己造成的伤害?
虽然事先准备了一段时间的恢复期,但面对如此巨大的创口,如此孤军奋战谈何容易?
由于没有任何人能为我提供帮助,我只能独自一人竭尽心力地一点一点去填补创口。哀嚎中的求救只有我一人能够听见,狰狞中的痛苦只有我一人能品尝到。所有的一切,只能单纯地用我那血淋淋的血肉构成。
但是,即使绝望,即使身后空无一人,我也一定要做到!一定!一定!一定!一定!必须如此!
2024.8.8
昨晚既没有不受控制地睡,也没有半夜11点多醒来。
虽然早上醒了几次,但最后还是在八点被护士叫醒的。
今天出院。如此看来,原来腹痛已经伴随了我整个住院时光了呀。
出院前,我看到了《谈话记录》。我看到了上面写有的“时有兴奋话多,语言显自大”的字样。
我感受到了夹杂着委屈的愤怒。
要知道,我平时在家可是非必要说话就不会岀声的啊。为什么要如此践踏我竭尽了全力所表现出来的精神焕发呢?我总不能在让我如此没有安全感的地方露出那被我视作弱点的柔软之处吧?
“自大”更是我性格的反义词。我为人极度谦虚,且带有一些我不愿提也不为人知的自卑成分。
他人为什么就不能看看我背后的努力与艰辛呢?
不过,像我这样的人,在这世上是注定要孤立无援的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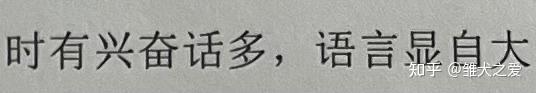
中午11点半,护士为我拔除了折磨我已久的留置针。
随后,我便迫不及待地扯下了手腕带,以及将病号服换回了自己常穿的白衬衫。
中午12:49,我出院了。
面对这段时间所带来的心灵创伤,那无休无止的腹痛无时无刻不在告诉我:你活该。
 新公网安备 65010402001845号
新公网安备 65010402001845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