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我们的现代生活”这句话究竟是什么意思?
对各位知友的“现代生活”是啥,还真没啥兴趣,但对所谓“大部分人是老董”这个观点持完全反对意见。
因为很简单一件事,在形成现下这个人类有史以来,最登峰造极的资本主义工厂国家过程中,农村早已被事实上改造成工厂生产部的外延部分,恰如潘毅教授在《壟斷資本與中國工人:以富士康工廠體制為例.》里对富士康工厂主要特征的归纳里提到“在很大程度上,工人的生活空間僅僅是車間的延伸。”,实际上,这恰恰也是“农村农业生活-城市工业生产”的写照
富士康為其工人提供了非常便利的生活設施,諸如集體宿舍、食堂、洗衣服務以及其他娛樂設施,然而道些配套齊全的生活設施,實質上是為了將工人的全部生活融人到工廠管理中,從而服務於「即時生產」的全球生產策略。在很大程度上,工人的生活空間僅僅是車間的延伸。吃飯、睡覺、洗衣等工人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像流水線系統一樣被安排好了,其本意不僅僅是為了滿足工人的日常所需,而是以最低的成本和最短的時間實現工人勞動力的再生產,從而滿足工廠生產的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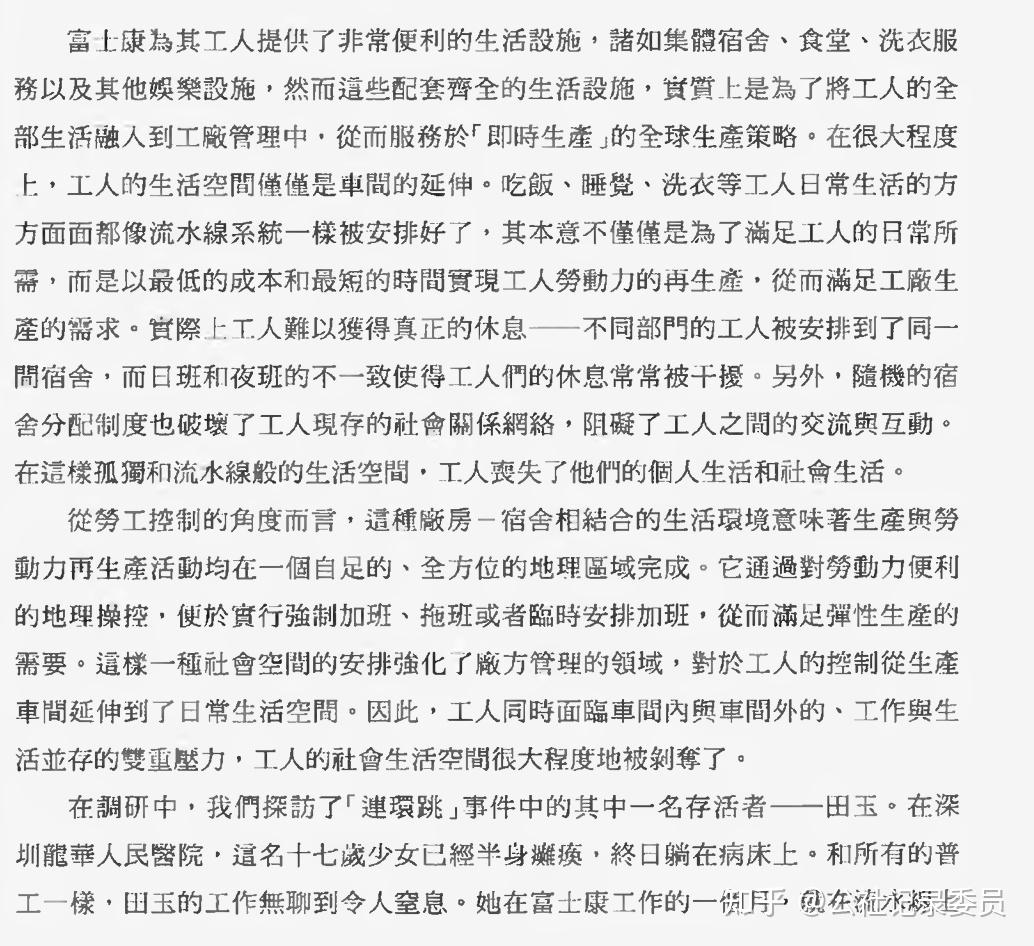
实际上,针对这一现象《世界工廠的「……特色」 新時期工人狀況的社會學鳥瞰》就进一步明确提到“具體來說,農民工的父母子女留在了生活成本較低的農村,成為「留守老人」與「留守兒童」,‘農民工家庭中的老人贍養和子女撫育也仍然需要部分依靠農業生產來實現。將農民工和他們的父母子女分開,不但可以有效降低工業生產成本,以廉價勞動力來推進工業化,而且可以減少城市的負擔和壓力。……這種「拆分型」的勞動力再生產制度給農民工家庭造成了巨大的困境,也導致了農村社區空巢化和凋敝的趨勢,但卻為以最大限度地獲取利潤為目標的資本所偏好,也被發展主義取向的國家所青睞。”
勞動力再生產包括勞動力的「維持」(maintenance)和「更新」(renewal)兩部分。前者指的是勞動者恢復體力腦力的過程,而後者則包括一系列勞動力代際更替 的安排,如贍養老人、撫育子女等。一般而言,勞動力的維持和更新兩部分應緊密結合,在同一時空條件和相同的制度背景中進行。然而在……,農民工的勞動力再生產過程卻被拆分開了。農民工個人體力腦力的恢復是在工廠/城鎮中實現的,儘管這往往只是以擁擠的住所和粗劣的飯食為特徵的勞動力低水準「維持」。而勞動力的代際「更新」則是在這些農民工的來源地即鄉村老家中實現的。具體來說,農 民工的父母子女留在了生活成本較低的農村,成為「留守老人」與「留守兒童」,‘農民工家庭中的老人贍養和子女撫育也仍然需要部分依靠農業生產來實現。將農民工和他們的父母子女分開,不但可以有效降低工業生產成本,以廉價勞動力來推進工業化,而且可以減少城市的負擔和壓力。也就是說,農民工的日常生活維持和代際更替被拆分在城市和農村兩個不同空間中進行,而以戶籍制度為核心的社會福利和 社會服務的城鄉二元結構強化了農民工勞力再生產的這種拆分體制。低工資收入、低社會保障、城市-農村雙向依賴、強迫流動等構成其主要特徵(清華大學社會學 系「新生代農民工研究」課題組,2013)。這種「拆分型」的勞動力再生產制度給農」 民工家庭造成了巨大的困境,也導致了農村社區空巢化和凋敝的趨勢,但卻為以最大限度地獲取利潤為目標的資本所偏好,也被發展主義取向的國家所青睞。
「拆分型勞動力再生産模式」的基本特徵是將農民工勞動力再生産的完整過程型 分解開來。這種再生產模式確保了勞動力的低成本優勢,在過去的三十年內將全球範圍內大量的勞動密集型産業吸引過來,推動……迅速轉變為「世界工廠」。國家則通過一系列規制安排和政策措施,如戶籍身分制度、高考招生政策、農民工子女就學政策、對勞工集體組織爭議權利的約束等延續和固化了這種模式。

而另一面,农村受城市工业生产影响,农村居民也渴望能够真正生活在城市工业社会中,故而在个人意愿、长辈意愿乃至农村缺乏个人发展前景的状况下,如同英国圈地运动一般,“第二代農民工的「圈地」感是非常強烈的。”
人們常常假定農村是城市失業農民工最後的依靠和保障。得益於現存的土地利用制度,村莊将承擔失業農民工勞動力再生產的社會成本。道一觀點為如下不斷重複的事實所支持:工人一旦離廠,通常會短暂地回鄉待上幾個星期。農民工返鄉的意願在春節期間尤為強烈・2008年初(中國春節前夕)百年一遇的冰災雨雪天氣也未能阻擋湧的返鄉潮。在許多工人的日記和作品中,「想家」和「夢到回家」等字眼也反覆出現。
然而第二代農民工很快發現他們的生活經驗無情地顛覆了這種假設——雖然這個假設在上一代農民工中可以得到部分支持。與18·19世紀英國工人階級形成時的情況不同的是,中國的新工人階級並沒有經歷一個殘酷的圈地運動過程。迄今為止,中國農民仍然可以擁有一小塊維持基本生存的土地。因此,與英國工人階級不同的是,沒有外在的強力逼迫中國農民離開土地走上無產階級化進程。然而這種不同並沒有造成結果的顯著不同。由於農民生活状況的惡化以及土地出產在農民生計中重要性的下降,第二代農民工的「圈地」感是非常強烈的。阿辛向我們講述當年返回家鄉的情景:
當我〔於2000年3月]回到家的時候,快到播種的季節了。我當時很興奮,因為我腦中產生了一個宏偉的計盡。我承包了一塊荒地,準備做點事情。晚上我興奮得睡不著覺,腦子中總是盤算著我的計畫:如果我能擴大經濟作物的種植規模,我也能發財。我將向我父母和其他村民證明返鄉也是一個正確的選擇。
阿辛動員他的親戚和鄰居,從他們那裡承包了大約二十畝耕地開始了他的創 業計畫。在综合考當地的情況後,阿辛決定種植西瓜。然而,由於西瓜生長季 節碰上大雨,西瓜成熟過快,以致不能及時銷售。父親從一開始就反對阿辛的計 畫,他在背後勸說其他人撤回土地。這樣僅僅幾個月的光景·阿辛就幾乎花光了他所有的幾千塊積蓄。他沒有其他選擇,只能離家返城打工。
阿辛的父親是一個典型的農民,同村裡其他同年齡的人一樣,他善良、勤勞,而且可能還有點固執,他在土地上耕作了一辈子來養家糊口,”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理解道片土地,也更熟悉道個村子。在他看來,留在道片土地上務農就永遠無法擺脫贫困的命運。父親對阿辛返鄉「創業」的強烈反對,其實和他常年勸說阿辛再次參加高考的態度是一致的。在父親看來,農村不是有為青年應該待的地方,在這裡沒有機會擺脫窮苦人的命運,無力避免苦命的生活(郭于華,2008)。農民生活的窮和苦讓阿辛的父親堅信·有高中文憑的阿辛應該盡力離開農村去追求更好的前途。在今天的中國農村,像阿辛的父親這種對待農村的看法並不在少數,這種看法的盛行是城市霸權的結果,也反映了資本主義全球化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背景下現代性向城市化和工業化的傾斜(Yan,2008)。
父親對兒子返鄉創業計畫的反對在某種程度上也是一種「圈地」:父親絕無可能讓兒子留在農村。阿辛返鄉的熱烈意願遭遇到父親的強烈拒絕,父親意志的勝利打消了阿辛回鄉的強烈願望,它導致一種類似的「圈地」效果:既是精神上的,也是肉體上的。
阿辛遭遇的這種「圈地」經歷絕不是個別現象。在那些決心回鄉做點小生意的農民工常中,只有不到一半的人最終回到了村莊(韓俊、崔傳義,2007)。而在道些少數返鄉者當中,很多又以生意失敗赔錢告終。我們在深圳和東莞遇到一些返鄉創業失敗後又回到城市的農民工。女工阿華就是道樣的個案,她回家嫁給了一個裁縫,然後在粤西老家養鴨子。她向我們講道:「我在家裡養鴨子,可是三個月就賠了五千塊。我一點養鴨的經驗也沒有。好多鴨子都死了,我虧本了。這樣我就又回來打工了。」當女工達到婚嫁年龄(通常在二十二到二十六歲之間)後通常會回老家結婚,然後搬到丈夫家居住,她們中的一些人就會留在那裡做點小生意而不再外出。不過,阿華在家只待了半年就又回到深圳打工了。金融危機以來政府採取了一些措施吸引费民工返鄉創業,但是上面那些阻礙阿辛和阿華返鄉的不利因素並沒有因此克服:農民工們既缺乏從事農業經營的經驗又缺乏技術,他們既沒有成功創業所需要的物質條件也沒有經濟資助,不斷波動的市場更也是他們所無法預料和掌控的。阿辛和阿華在家鄉創業——種西瓜和養鸭子——的失敗就是由這些因素導致的。在阿辛的河南老家,全村只有幾戶人家是完全靠農業謀生,其中就包括阿辛的叔叔家。按照阿辛的說法,叔叔是個特別勤快的人,「看到什麼賺錢就做什麼」。這些年來,阿辛的叔叔嬸嬸先後養過豬、羊,將稻田改成魚塘養魚,魚不賺錢又部分地種藕、種樹,但是不管做什麽,一家人辛苦一年往往掙不到一萬元。如果阿辛繼續留下來種他的西瓜,叔叔的遭遇也許就是他可以看到的前景。
阿辛沒有其他選擇,只能再次離開老家。阿辛受到沉重的打擊,但是他只能将痛苦深埋心底,背起行囊再次來到深圳。在去深圳的火車上,他無意中得知在深圳做手板(通常是用泥、陶等材料製作玩具模型,供大規模生產用)工资高,阿辛有一點美術底子,就設法進入一家生產手工藝品的工廠上班,試用期工资八百元。在試用期過後,他成為手板師傅·工資穩步增長。常他在道家工廠幹到第三年(2002)時一個月已經能拿到一千七百塊了,加上加班费有時可以掙到三千塊。
在同齡的打工仔中,阿辛能成為熟練的師傅並拿較高的工资,可以說是幸運的。但是,曾經受到的心理創傷、嚴酷的工廠環境、無處安放的生活目標,使得他在後來的工作中沒有真正地快樂過。對阿辛來說,工作逐漸失去了意義:「不管我在哪工作我都感覺不到快樂。我的心永遠不能平靜下來。我總覺得我應該做點大事。」
如同我們在東莞碰到的一個女工所說的那樣,第二代農民工面臨著深刻的兩難處境:「當我出來打工的時候我很想家。可是當我回家的時候,我又想著出來打工。」對於第二代農民工來說,「種田沒有出路」已經成為一個共識。他們知道,一個稍微像樣的房子·還有結婚開銷、基本教育费用、醫療開支,以及日常生活開銷,都遠非種田收入可以承擔。總之,對返鄉農民工來說,農村缺乏個人發展機會造成了一種類似於「圈地」的效果,其結果就是我們所理解的自我驅動的無產階級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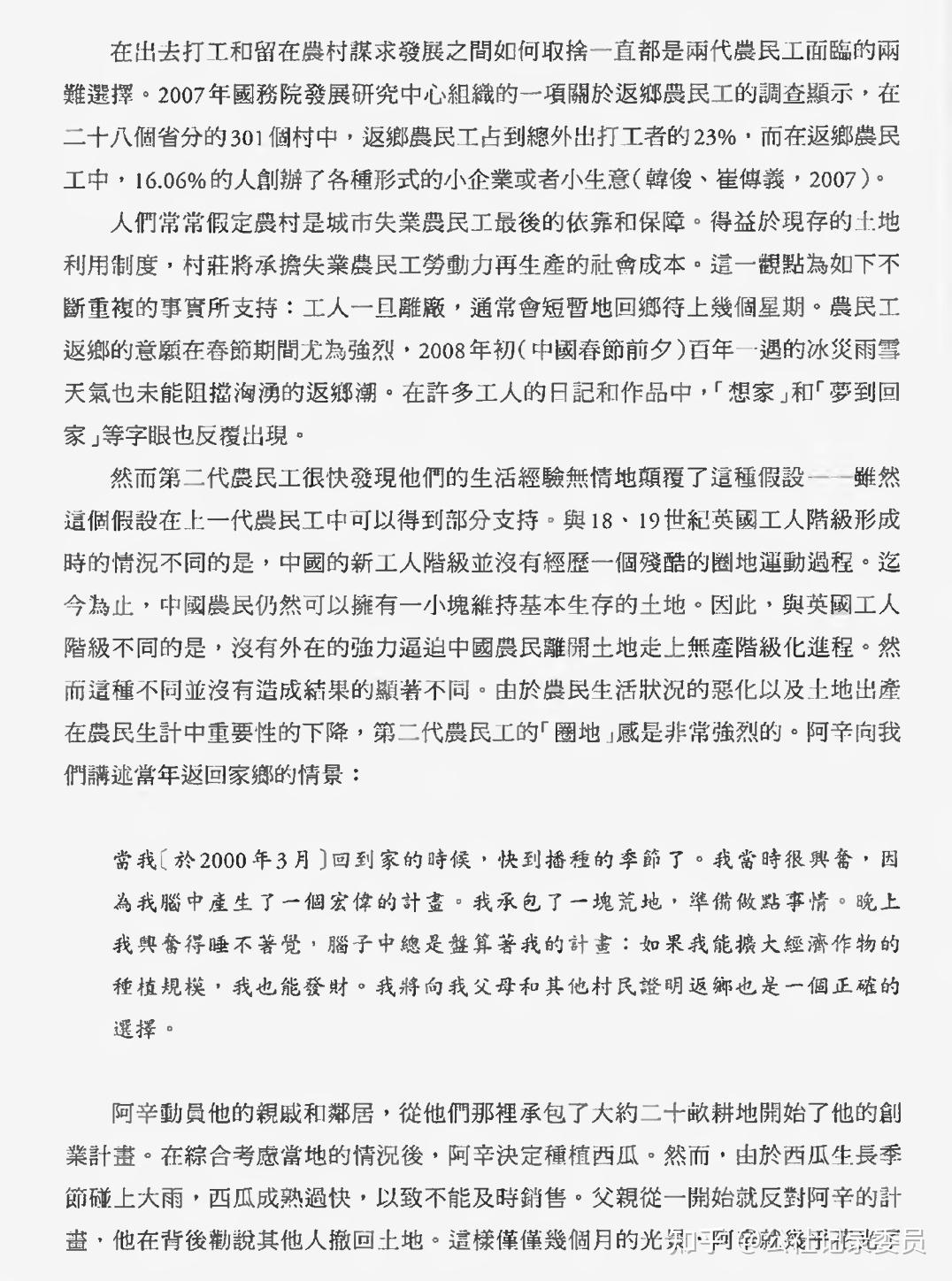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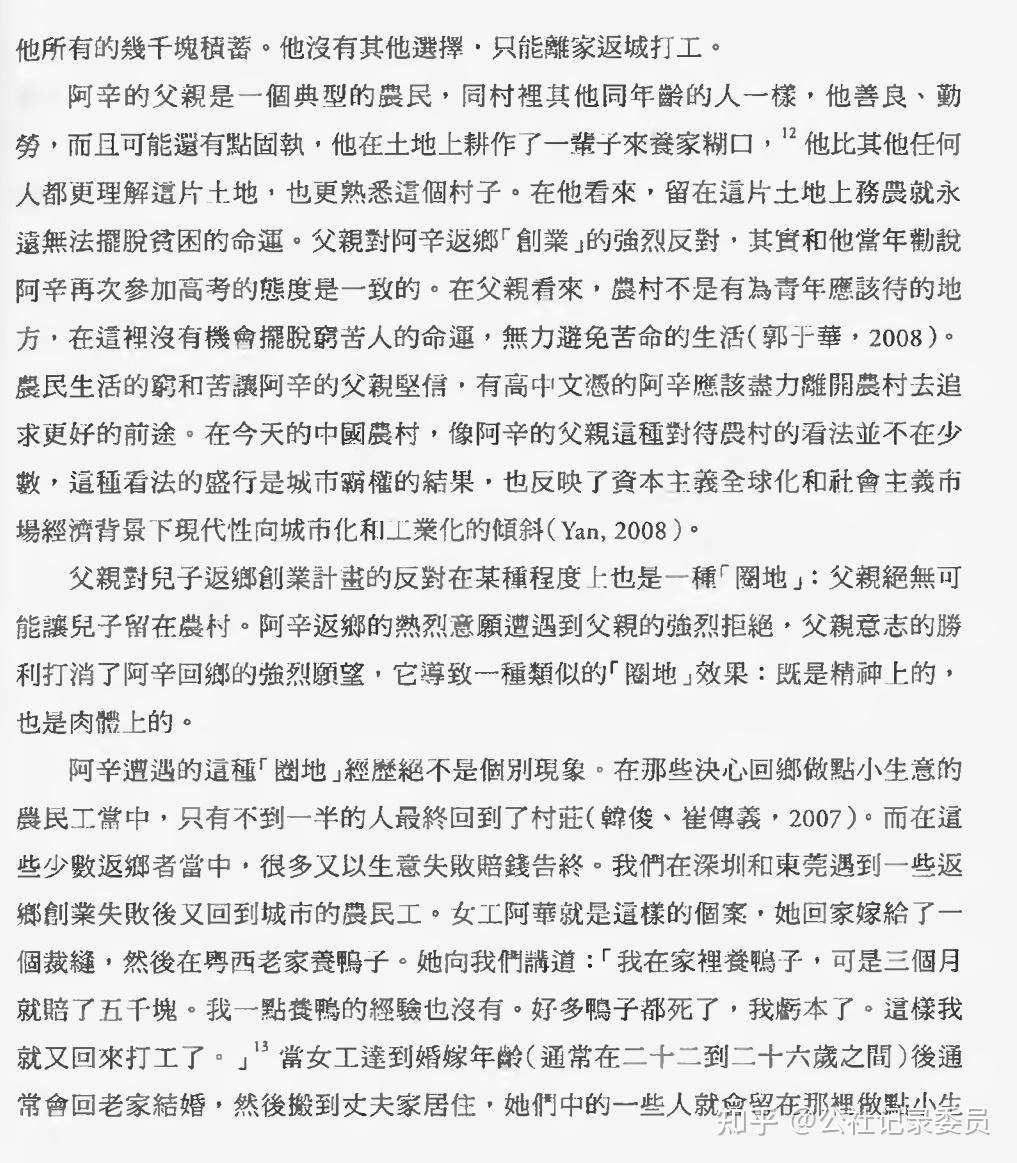
更有趣,也更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于,长时间的城市工业生产生活也重塑了这一代新工人“如果說第一代農民工如前面提到的阿英還不能公開地集體地表達她的諸般消極情感的話,第二代農民工則已經在要求改變了。”
焦慮、孤獨和痛苦是第一代民工生活中揮之不去的主题。如果說第一代農民工如前面提到的阿英還不能公開地集體地表達她的諸般消極情感的話,第二代農民工則已經在要求改變了。第二代農民工工作和生活中的痛苦和愤怒是如此明顯。如果說阿辛的故事特別值得關注的話,那只是因為他在高考經歷、工廠打工以及返鄉創業的失败嘗試中遭受到嚴重的社會創傷。所有這些經歷使得他的愤怒累積到一個突破點:「我相信我應該幹點什麽大事。我的生活應該有更大的理想。」他反覆地強調自己不快樂,難以維持內心的平衡。
和阿英不同,阿辛内心的不安不再被壓抑,它得以表達出來,甚至轉化為外在的行動。2007年初,當阿辛發現他所在的工廠準備搬出深圳的時候,他就開始動員工友,開始了一系列的集體行動。阿辛和老黄、老陳等四位工友起訴當地的勞動局,指控他們漠視工人的需要,沒能執行那些保護勞工的行政法律措施。這五位工人後來被媒體稱為「維權五君子」,以爭取勞工權利而聞名。五人都在工廠的手板部上班,都已經幹到手板師傅的位置。五人都年過三十,其中最年長的老黄已經在這家工廠工作了五年,每個月可以拿到四千兩百塊,最年輕的是阿辛,在這家工廠工作了一年,工资兩千兩百塊。
在工人們的團結鬥爭中,宿舍發揮了一個特別重要的作用。阿辛提到,下班回到宿舍後工友們常常一起聽收音機,尤其是收聽有關法律和打工的節目。阿辛告訴我們,聽這些節目對他們來說是一種「啟蒙」,他們從中學到企業沒有簽訂勞動合同是違法的,而加班工作則應該獲得雙倍或三倍工資等等。2007年2月12日·五位工人向工廠提交了一份公開信·要求集體解除勞動關係·其理由是工廠沒有跟他們簽訂合法的勞動合同,而且沒有依法支付他們的社會保險金,此外還強迫他們超時工作·沒有為每天的加班以及週末和節假日加班支付加班费等。同時,阿辛和他的工友還敦促當地的勞動局官員幫助維護工人的合法權益。他們尤其提出勞動局應當確保工廠依照《勞動法》縮短工時,同工人簽訂合法的勞動合同,為工人上繳社會保险,為2007年1月和2月分的超時工作支付加班费等。尤其引人注目的是,這五位工人要求工廠支付過去兩年的累積加班费,其總額達到人民幣六十五萬元。對於自己的上述要求他們表達得很清楚:
工人被要求一月至少工作二十八天,每天至少十三小時。加班费只是在每天工作超過九小時以後才有。不但如此,工人的工資每小時低於法定工资1到1.2元。對於計件工人而言則根本沒有加班費。
以老黃為例,2006年12月他工作了227小時[被認為是正常上班時間〕,外加114.5小時加班。2007年1月,他工作了266小時,外加87.5小時加班。
工廠搬遷是工人集體行動的催化劑,此前工人在工作場所不斷累積的愤怒、挫折和不公平感一下子找到了一個爆發點·工人們擔心工廠搬遷後可能裁員,更擔心搬遷後追討加班工資變得更加困難,這促使工人們採取行動。老黃說道:
我們都是工廠裡少數比較核心的熟練工人。我一個月可以掙到四千多塊,我不用擔心吃喝問题,但是我們缺乏安全感,也沒有一種體面的個人形象。儘管我們把自己的青春和汗水奉獻給了深圳,但是我們還是沒有應有的地位,而且最終來說是召之即來,揮之即去,隨時可以取代的。當我們老了,得了慢性職業病,然後返回老家,然而我們既沒有養老金,又沒有健康保險,那時我們怎麼辦?6
老黃說得很清楚,他並不是對他的工作條件或者工資不滿意,令他擔心的是未來,是一種既沒有安全感又沒有尊嚴的職業前景。作為一個可以被取代的勞工,他知道他的位置是很脆弱的,是他的職業生活既無未來又沒尊嚴激起了他的憤怒和不平。
某種程度上,道五位工人面臨大致相同的處境:都正值壯年,都達到了自己職業生涯的高峰,等待他們的將是不可避免的下坡路,或者被更年輕的工人所取代。就是在這種進退兩難的處境之中,他們決定採取激進行動。在要求勞動局判令工廠賠付未得結果之後,他們很快將行動的目標從工廠轉到勞動局身上。五位工人充分地利用互聯網路查詢相關資訊·得知常地勞動局有责任監督勞動條件並處理勞動糾紛。工人們也算計到,通過起訴勞動局可以降低維權成本。
在進入起訴階段,這家迪士尼供應商的六百名工人(其中多數是女工)也組織了各種抗爭。2007年5月該工廠同工人簽訂了一份短期勞動合同,並正式宣布將於年底搬遷到東莞。9月,工廠的女工們團結起來組織了多種形式的抗議活動,包括集體停工、抗議、撤回勞動合同等。她們要求支付拖欠的加班费,要求經濟赔償,要求公司補交她們應得的社會保險金(見《南方都市報》2007年9月12日的報導)。工廠的回應是解除了與一些女工的(非法)合同,並只支付一個月工资的補償金。「老闆們沒一個有良心,」當工人們拖著行李走出工廠宿舍的時候很多都會這樣抱怨。被抛棄的感覺不僅在離廠女工那裡非常強烈,在那些留下來的工人中也很普遍・工廠管理層態度強硬,他們說根據《勞動法》・只需提前二十四小時通知工人就可以停止勞動合同,因此工廠沒有责任支付補償,一個月工资已經是工廠給予的恩惠。這種說法使得女工們更加憤怒。
在這年七月五位工人第二次向法庭提出起訴。他們提交了一份詳細的報告,說明勞動局對他們的不滿和爭端怎樣進行了不常的處理。他們要求法院否定先前的判決。更重要的是,他們堅持要求經濟補償,並要求有保護自己利益的權利:「我們並不指望在與政府部門打官司時能取得勝利,也沒有指望能完全得到我們要的經濟補償。我們希望的只是探索一種新的可能性——探索一條保衛我們自己權益的新的道路,並且希望這條路對其他工人能有所幫助。」(見《南方都市報》2007年7月25日的報導)
如果說工人的這場集體行動就是為了經濟利益就太簡單化了。對阿辛和他的工友的工作和生活了解得越多,我們越能體會到在他們採取行動的各個階段所表達出來的愤怒和不滿。對阿辛來說,促使他採取行動的既非金錢,亦非個人名譽。他是被他那「做點大事」的願望所推動的,他希望以此「引起人們關注勞工們艱難的生活」,「為打工仔爭取到一點公平」,並且「懲罰那個沒有良心的老闆」。
2008年4月,在等待司法判決一年未果之後,這五名維權工人中的三人——阿辛、老黄和老陳——決定去北京打官司。他們希望能夠從中央政府那裡尋求幫助,這也是他們最後的機會了:「去北京是最後一步。我們幾乎把所有能想的法子都用過了。現在這是最後的辦法了,我們不想就此結束,」老黃這樣說道。他們在北京待了五天,在這期間他們去了勞動社會保障部、全國人大信訪辦公室、最高人民法院、國務院、全國總工會。然而結果卻讓他們失望:他們要麼根本無法遞交陳述信,要麼就被草草地打發。然而,阿辛和老陳認為他們的北京之行還是「有一個收穫」,「在我們來之前我還是抱有某些希望的,現在我們死心了」。工人怨恨的政治轉變為一種絕望,然而在對於外在保護或拯救力量「死心」的同時,訴諸於己的心思正在萌芽,這種心態的變化,實際上普遍發生在參與集體行動的工人中:「我們只有靠自己。我們沒法相信政府,沒法相信老闆。我們要的只是一點公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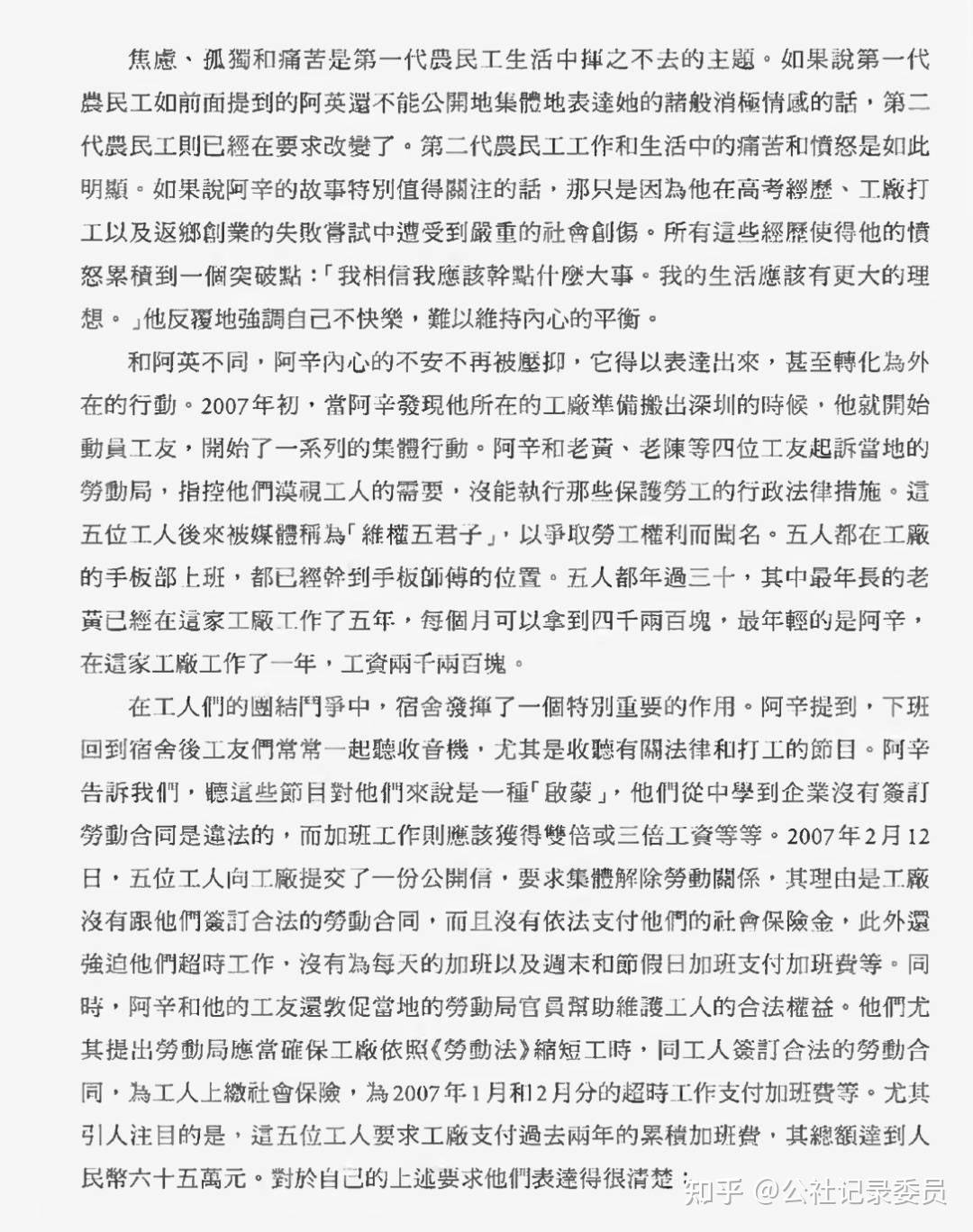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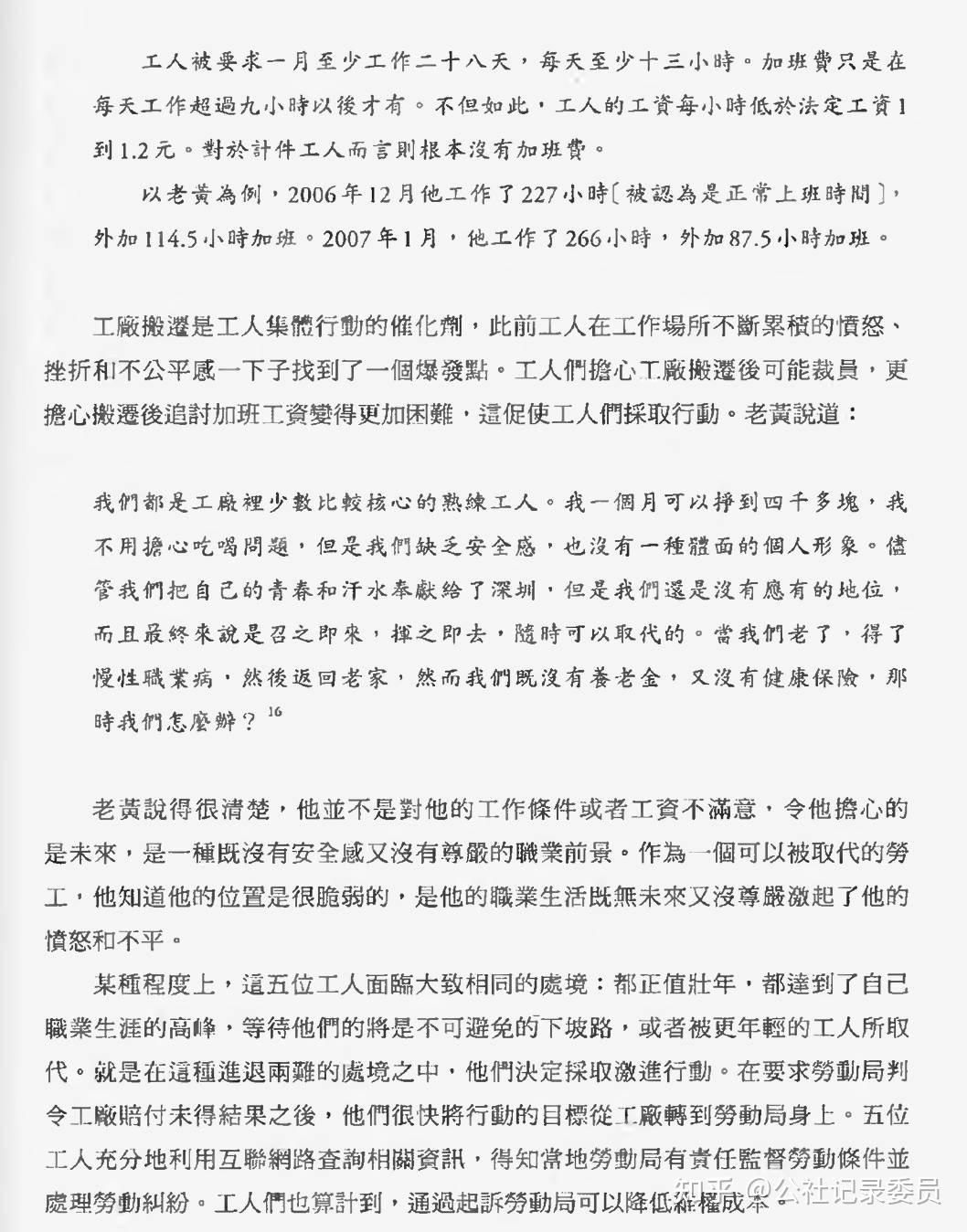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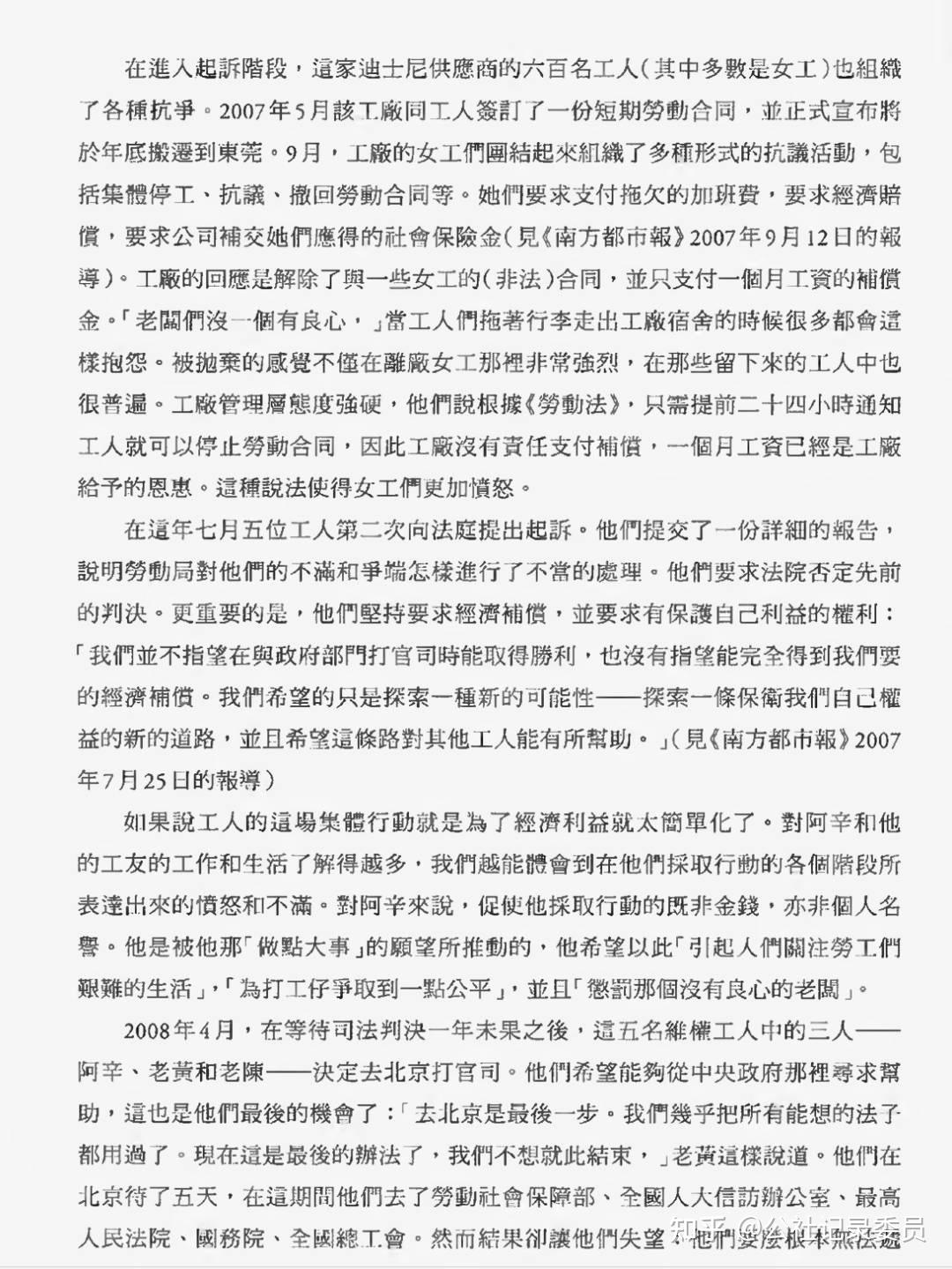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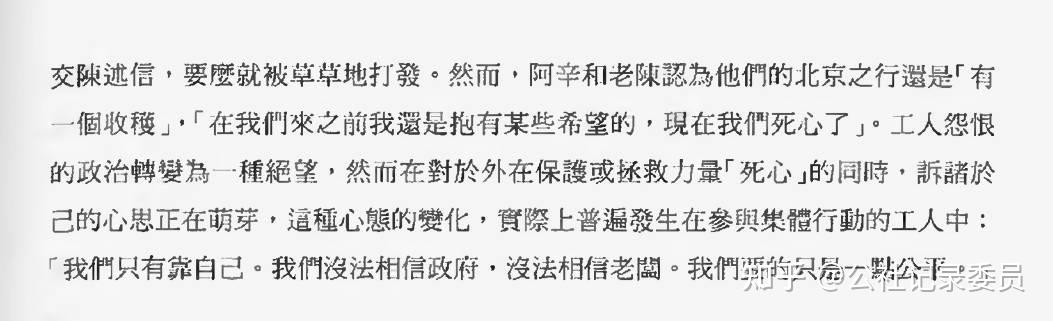
所以,我个人觉得,在一个“成熟”到登峰造极的工业国,去指责大部分人是董贼这样的准还乡团,多少沾点……
后话
倒也不确定各位同志、朋友都读出来了什么,但反正我看到最后一段的时候“工人怨恨的政治轉變為一種絕望,然而在對於外在保護或拯救力量「死心」的同時,訴諸於己的心思正在萌芽,這種心態的變化,實際上普遍發生在參與集體行動的工人中:「我們只有靠自己。我們沒法相信政府,沒法相信老闆。我們要的只是一點公平。」”
确实像晴天霹雳一样,整个身心都被震撼,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让思想冲破牢笼。
 新公网安备 65010402001845号
新公网安备 65010402001845号